今人贴在社会学家吴景超身上最主要的标签,莫过于“前瞻”一词。这种八九十年之后姗姗来迟的知音感,也反映出吴氏思想与民国之间的错位。塑造这种前瞻或错位之感的,多为吴景超关于“工业化”“都市社会学”“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结合”等宏观经济方面的论述。这些仅为吴氏所留文本的一部分,其余文本尚待进一步发掘。
新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吕文浩编选的《历史意识与世界视野:吴景超谈史论世》一书,收录了吴景超较少为人所关注的论述,并为之撰写长篇导读。这一整理工作不仅使吴氏的形象更为丰满,亦让我们意识到他思想的同时代性。在那个知识人身份认同与行为取向发生重大变化的“过渡时代”,与不少人一样,吴景超的心态徘徊于学人与士人之间,始终心系现实的政治与社会。本书则为勾勒他在“过渡时代”的人生轨迹提供了很好的史料基础。
撰文|薛克胜
《历史意识与世界视野》
作者:吴景超
编者:吕文浩
版本:学苑出版社 2025年4月
实证主义的信徒
诚如罗志田先生所论,伴随着传统经典指引作用的瓦解,如何界定“学问”以及怎样治学,均成了需要重新厘清的问题。或源于此,近代受过西式学术训练的读书人,往往不大满意传统的治学方法。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即是一例。1935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径直指出,之前的中国学者为传承观念所支配,“只重视学派的来源,而忽视研究的方法”,结果导致许多有价值的学问泯灭无存。
具体到社会学研究而言,吴景超认为社会的问题错综复杂,各方面相互联系,所以学者不可拘泥于一法,而应根据问题性质择取方法。但无论如何,首先要有一种不存偏见的客观态度,“只问事实的有无、因果的关系,并不判断它的好坏”。其次应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言必有据,立论必有所本。可见,吴氏研究社会学,追求一种排斥价值介入、以事实为本的实证主义。
吴景超(1901年-1968年),安徽歙县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先后执教于金陵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与闻一多、罗隆基一同被誉为“清华三才子”。图为吴景超(后排中)及其夫人龚业雅(前排右)与亲友合影。
除基本的治学态度以外,吴景超还总结了社会学者常用的几种研究方法:历史法、人类学法、统计法、个案法以及抽样法。前两者用以研究过去的社会现象,后三者则用以研究现实社会。吴氏本人则以使用历史法和统计法而著称。这一特点亦鲜明地体现于本书之中。囿于学力,下文仅以举例方式稍加展示吴景超历史研究的风格。
吴景超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总是理解当下乃至展望未来。正如他所言:考察历史的“研究所得,常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目前的问题,有时还可以帮助我们制定将来的政策”。即使是正文无一语提及现实的《两汉多妻的家庭》(1931年4月)和《两汉寡妇再嫁之俗》(1932年4月19日)两篇文章,也颇具现实关怀。前者总结了“多妻”对于家庭社会的七种恶劣影响,后者则发现汉代社会并不鼓励女子守节,进而强调国人的贞操道德观并非一成不变。这两篇文章讨论的虽是汉代,呼应的却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新式知识人所倡导的女性解放言论。上述两篇文章固有史料根据,但其选题方向,实与吴景超自己所秉持的价值观有关。他在本书第二编《中国社会中的几个问题》(1927年1月)一文中,曾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一妻多妾”制伤害女子人格,应当修改。这其实是将评判婚姻的标准,由传统的家族嗣续变为现代的个人幸福。指出此点并非苛责前贤,而是试图说明,即使标榜客观、科学的社会问题研究,其选题和论证方向也难以完全避免研究者价值观的无形指引。
以学导政的尝试
学者方慧容在《社会、经济与政治之间:早期社会学者的徘徊和探索》一书中指出,“科学主义”是吴氏最重要的思想底色之一。吴景超主张,无论企业经营,抑或治国理政,只要相关负责人能在科学理念和专家人才的指引或帮助下,不断改进具体实践层面的举措,使之合理化、科学化,便能收获成效。总之,方慧容总结认为,吴景超身上保留了儒家偏重人事的思考特征,试图通过完善相关人员的品格和知识,促进政治与经济建设。若参照中国儒家“成德”的政治传统,吴氏似乎认为,内化科学思维、践行科学方法已成为知识人甚至某些从政人员不可或缺的现代德性。
《社会、经济与政治之间:早期社会学者的徘徊和探索》
作者:方慧容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2年8月
在吴景超看来,作为合格的现代国家治理者,“现代的眼光”不可或缺。其专著《社会组织》“政府”一章下,专列“政府与科学”一节,主张“政府应当把科学看作必需品,看作一切行政的前驱”,强调行政需以研究为基础制定计划。他认为“科学与政治像这样打成一片之后,政治才有昌明的可能,社会才有进步的希望”。可见,吴景超尤为强调现代社会需延续“政学相济”的传统治理经验。1931年他撰写《大家来做南京的研究》一文,呼吁南京市政府社会局职员从事研究事业,“把南京社会各方面的情形,一步步地研究下去,把他们的结果报告出来”。而在吴氏所规划的农政局人事中,应至少有三个知识人,分别从事乡村社会调查、农事试验场成果推广和乡村组织化工作。
不过,上述意见大多停留于呼吁层面。与之不同的是,吴景超本人的确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了以学导政。收录在本书中关于“耕者有其田”理论与统制经济和战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救灾实践的相关讨论,便清晰体现他如何从科学的角度指导或评价政府施政。
其中,有的意见是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实现国民政府所主张“耕者有其田”的方案。对此,吕文浩已在导言中有所梳理,此处不再赘述。有的意见则是直接影响了施政实践,比如战后作为行总顾问,吴氏前往湖南衡阳考察救灾情况后对如何提高效率提出建议。虽然行总湖南分署所派遣的工作队较少贪污行为,但人数过少,无法起到急赈作用。因此他建议仍由地方原来的政府组织(乡镇保长等自治机构成员)发放面粉,而工作队则负监督、抽查、检举之责。该建议被相关主事者采纳。
书生本色及其政学实践的困境
1935年12月,蒋介石改组负责实权的行政院并兼任院长后,招揽翁文灏等人加入政府。他们在国际交涉和财政金融方面,依靠专业知识为蒋出谋划策,形成著名的“政学系”。他们虽有政府正式任职,但其角色定位多近于吴景超《论幕僚制》一文中的幕僚或智囊团,“根据研究结果”影响长官决策。至1947年离开政局重返清华校园,吴氏共有11年从政经验。
在从政期间,对吴景超刺激最大的事件之一为“平价大案”,其后来弃政还学便与此密切相关。1930年末物价持续高涨,蒋介石以物价高涨不平,官员办事不力、营私舞弊为由,要求“军统”彻查包括农本局在内的政府平价机关的账目。随后,农本局工作人员被戴笠逮捕,该局负责人何廉及其直属上司经济部长翁文灏亦遭牵连。结果,何廉的职务与农本局本身均被撤销。
在当事人何廉看来,此事直指政治根本。若行政工作有差错理应撤换他个人,但一并裁撤机构说明了蒋介石“并不真正懂得为经济建设建立主要机构的重要性”。
根据吴景超清华时期的学生,经济部同事李树青的回忆,以及今人的相关研究,“平价大案”背后其实是蒋介石亲信孔祥熙等人与从政学人领袖翁文灏两派之间的斗争。国民政府内部根深蒂固的派系斗争亦影响到吴景超的考核评价。与学人较为集中的经济部的赞扬不同,“中统”成员潘浙在1940—1941年考绩报告中称,吴氏“行政经验与处理事务能力均差,为政学系有力分子”。上述案例反映出在制度建设未上轨道之前,试图加入政府以专业知识影响政府的学人,难免卷入人事斗争,并常因政治基础薄弱而处于不利局面。
吴景超1947年作品《劫后灾黎》内页。
不止行政实践易受现实政治纠纷裹挟,即使是吴景超以实证主义认知社会现实的方式,亦引发了时局剧变下某些激进青年的不满。1947年6月,一位署名“域槐”的青年在吴晗主编的地下刊物《自由文丛》上发表了《吴景超教授回到北京以后》。该文认为吴氏虽热心于社会调查和研究,但“总不免带着一些传统文人和浓厚的经院风气。始终只是以观察人的身份去观察实际的问题”。如此则易被政府宣传所欺骗,难以真正了解社会现实。这一批评固然有其政治立场,但确实也有一定道理。在处理政府敏感或利害牵涉较广的现实议题时,注重实证的学术研究易受相关材料留存或公开不足,乃至材料失真的消极影响。
近代中国是个从政治到文化发生诸多巨变的“过渡时代”。吴景超以书生本色,穿梭于政学之间,不懈探索解决中国问题之道,展示了他在“过渡时代”的努力和抉择。不同于大多数在野知识人,吴氏身为政学系一员,对于改良社会和建设国家还是发挥了一些直接的实际作用。不过在国民政府眼中,从政学人往往只被视为一种暂时满足现实需求的工具。而他们立足于理论和长远的言论则多被束之高阁。但若以长时段视角审视吴景超,其最主要的遗产仍在于对中国近代转型,提出的周详而独到的学者洞见。
撰文/薛克胜
编辑/罗东
校对/薛京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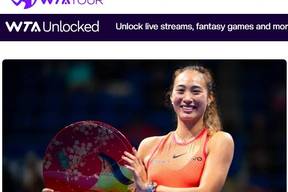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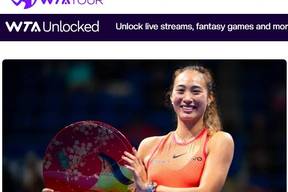
百度分享代码,如果开启HTTPS请参考李洋个人博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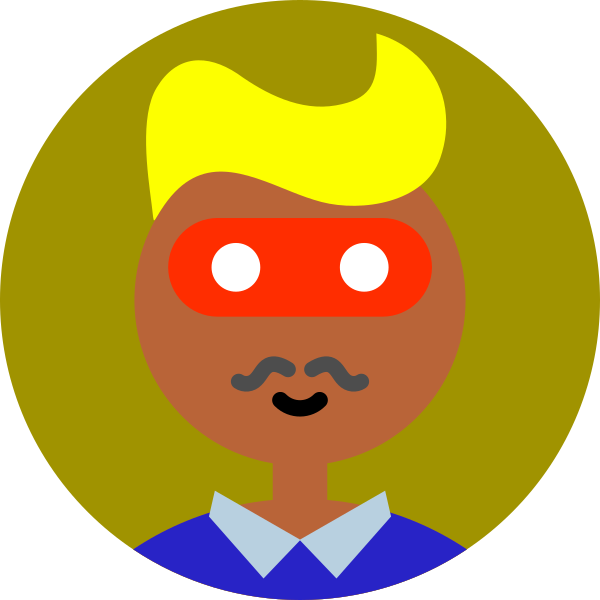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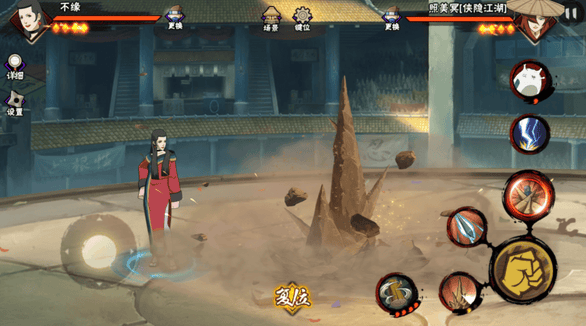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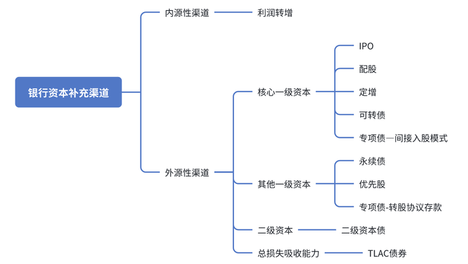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